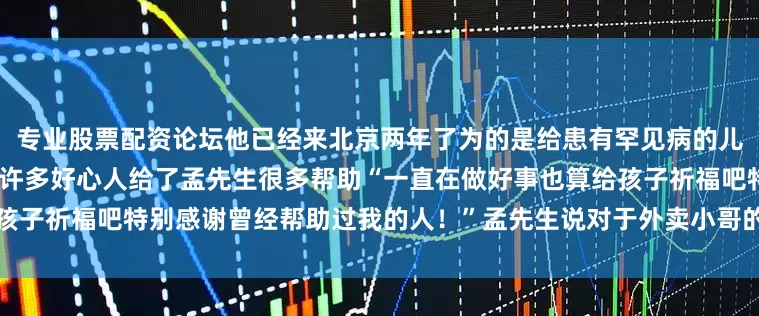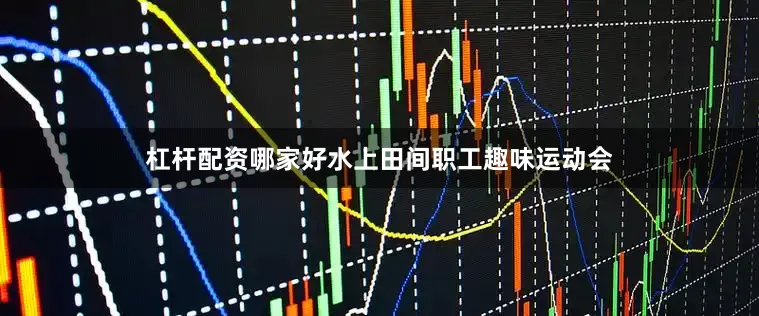岳父扛着水上阵,瞅见指挥官有点面熟,凑过去却被人挡住了。
他眯着眼睛瞅了瞅,嘀咕了一句:“这个大头儿子,是不是叫周啊?”

岳父冒着大雨跑到战场,看到长官愣了一下,1946年的山西荣河县,刚打下来的阵地上烟雾弥漫,炮声还在耳边回响,伤员们也还在抢救中。
老百姓才敢从地下室爬出来,提着自家的水缸和破壶,扛着一堆破布,一个一个地给前线的小战士们送饭送水。
这天,一个大叔从城外溜达过来,肩上扛着两壶水,脚底下都是泥巴。
衣服洗成了灰白色,脸上写满了急迫。
他是周希汉的老丈人,名叫周振乐。
女儿自从1941年嫁人后,就像一颗大石头掉进了水里,再也不见影踪了。
那会儿办婚礼跟赶集似的,新郎一觉醒来第二天就消失了,搞得人家说要去打仗,真是个神秘的人!

时光飞逝,女儿的信件越来越稀少,最后干脆连影子都没了。
我听说他去了延安,也有人说被敌人围住了,听着有人在八卦他们有了个小孩,还有人说这小家伙没能挺过来。
当爹的,心里跟提着个大石头似的。
那天,他听说共军的十旅把荣河县给拿下来了,那个旅长名叫周希汉。
名字一出,周振喜的心都吓得跳了个筋斗!
在丈母娘那儿我听说过,新姑爷就是这个名儿。
他那时一句话都没说,回家抓了两个水壶,弄得像是要给前线的人送水去喝呢。
老伴儿说:“你要是认错了咋整?”他没搭理,扛起扁担就走了。
到村口,守门的拦住了,问他来干什么,他答曰送水。守门的一瞅他的肩膀,点了点头,放他过去了。
再往里走几步,远远瞧见前面土坡上站着几个家伙,一个年轻的军官穿着灰色军装,双手背在身后,正琢磨着地图呢。
两边就像摆放着两个“铁塔”,站得笔直不动。

那哥们儿个子高得像竹竿,脸黑乎乎的,鼻子还特立,周振喜瞅了半天,总觉得在哪儿见过,可又不敢确认是不是他。
他想凑过去瞧瞧,刚迈了两步,哨兵立马举起枪说:“你站那儿别动!”
“谁是那个头儿啊?”
“他发问了,像是在跟鸡聊天一样!”
哨兵一捋胡子说:“十号部队的头儿!”
“咱旅长又添了一句啥话呢?”
一听到这三字,他的手一抖,差点把水壶干翻了!
喘了口气,脚步又挪了两下。
那位旅长正埋头看着地图,顺便瞥了我一眼,啥话都没说。
周振喜愣住了,瞅了两秒,随即小声问:“您是不是叫周老头?”
那位军官抬起头,眼神一愣,瞅了他一眼,猛地眯起眼,好像想到了啥,嘴角微微一翘。

现场静得连蚊子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。
周振喜没再唠叨,转身把水壶放妥,一个一个整齐地排好,随后默默后退几步,站那儿不动了。
周希汉咳咳一声,转身背过了脸,不想让老爹看见。
过了一会儿才说:“把水壶留下,让他先溜!”

信件飞了好多年,第一次碰面居然冷得像冰块,一个旅长第一次见丈人,不是在婚礼上,也不是在家里,而是在战地的指挥台上,连一句闲话都没扔出去!
十旅的几个保安一脸困惑,不明白这位老爷子是哪位,也没听见旅长跟他打招呼。
水来了,人走了,队长依然专心看地图,把电台的命令翻个遍,像是一场戏,啥都没发生过似的。

那晚,守卫的营地里有个老家伙偷偷溜去听风。
那老家伙是咱旅长的丈人!
当年我姑娘在运城女师读书,叫柴英,后来把名字改成了周璇,就像换个新衣裳一样!
周璇家里条件挺好,老妈是教书的,她读书全靠捡奖学金,平时过得跟个穷和尚似的。
1941年,学校旁边的部队来了,周希汉带着兵儿们上山干活,完成任务后路过运城,结果跟她搭上线了。
才认识没几天,周就飞信要求结婚了!
那会儿他正泡在部队里打仗,根本抽不开身,也没法回家乡溜达。
这封信是从战场上的邮差那儿来的,字迹潦草得跟鸡爪子写的一样,但情感直截了当,没啥拖泥带水的。
女家那边起初有点怂,没敢答应。
新郎这小子影子都没见着,婚礼搞得像个马戏,老娘家的人心里嘀咕怕被卷进去,唉呀,这共产党打起仗来可真让人胆寒,生怕自家姑娘受了罪。

周璇那是个死心眼的主儿!
她说:“这个家伙,靠谱得很!”
我对你百分百放心!
那年冬天,两个人在太行山的某个小村庄里简简单单搞了场婚礼。
结婚刚俩天,周希汉又被催着走了!
之后那几载,两人就靠纸条传情了。
信件像乌龟,回来像蜗牛,老是得靠嘴巴传话。
1943年,周璇生了一对双胞胎姑娘,一个叫周鄂,一个叫周晋,简直是个“双重幸福”的节奏!
那年冬天,敌军来了个大扫荡,村子里粮食见底,小孩儿都饿得跟小鸡似的。
两个小家伙没撑过几个月,就陆续跑路了。
消息送到前线,周希汉回信就是一句:“仗打完,我回来背家!”
后来部队往西走,周璇揪着小孩一路跟着,晃荡了整整八个月,才咕噜咕噜到了延安。
在延安,她又添了个小子,给他起了个名叫“周太安”。
战斗打得热火朝天,消息传得稀巴烂。
丈母娘跟老丈人还不知道孩子已经挂了俩,只听说女儿去了延安,活得好好的呢。

直到1946年,战乱冲到荣河,周振喜听见有人说:“看咱们这位旅长姓周,打仗的时候跟不要命似的!”
他心里一紧,抓起水桶就蹦跶着出门了。
出门前他对媳妇嘟囔了一句:
要不是他,那就当给人家送水去了!
要是能苟活着见上一遭,那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!

那天攻陷赵城的时候,俺家小子刚出生,陈赓给太岳前线打了个电话恭喜,战斗烧得正紧,第十旅负责冲锋赵城,这地方复杂得跟迷宫似的,守军也是死磕到底。
周希汉整天整夜地在这儿摆弄军队,三天三夜没眨眼!
就在那天攻陷赵城的时候,电台有消息传来,延安那边哭喊着:“周璇生了个小子,俩都没事!”
战场上,第一次听到家里传来的这一消息,周希汉憋着没出声,低头把作战图纸给收好了。

陈赓也在指挥部,听到这消息后立马拨通了电话,直接来了个亲自上阵!
电话那头就一句:“周旅长,恭喜你这小子!”
赵城也搞定了,兄弟们也来了,这下可是双喜临门啊!
周希汉一声“谢大佬”,然后就闪人了。
接下来几天,他一句家里的事都没扯。
部队得继续向前冲,不能拖沓,也别放松警惕!
指挥部换地方,士兵们也换班,他像个老鹰,盯着每一个小细节不放!
旁边的保镖们都知道旅长刚当了老爸,谁敢多说两句啊!
赵城那场战斗一结束,第十旅立马像开了飞一样往南冲,准备把敌人的粮草路给堵上!

这会儿,有消息从战区传到后方,周振喜又蹦跶着来了,这次跟上回一样,连个通知都没给,身份也没透露。
这次他没带水,揣着一包馒头和一小瓶自己家的泡菜。
依旧那条尘土飞扬的路,还是老地方!
他走到岗哨那儿,岗哨一眼就瞧出来了,轻声咕哝:“老兄弟,你来了啊!”
他轻轻摇了摇脑袋,保安就带着他一路蹦哒到了指挥部的临时窝。
那是个坡底下的土屋子,刚收拾过,地上还有湿漉漉的泥巴呢。
周希汉从一堆地图后冒出来,瞅见门口有人影在晃,愣住了,不出声,就这么盯着。
周振喜一声不吭,把行李放下,把那个酱菜瓶挪到桌子边儿,盖得稳当,当时屋里静悄悄的,就听见纸页啪啪作响。
看门的憋了一肚子话,开口了:“旅长,这位是您老丈人,上次来送水的那位!”

周希汉点了下头,算是搭了个腔。那晚,他没呆在指挥部,而是搬去隔壁的小房间打盹。
第二天出发前,周振喜把一张皱得像刚从洗衣机里出来的小纸片塞给了警卫,叫他帮着转交给旅长。
保安接过来后,偷偷塞了一张纸,上面写着:“只要你把她照料得妥妥的,我就可以安心了。”
孩子们像放电影一样不断冒出来,打仗从没停过,家里也是忙得不可开交,直到1946年,这个家才终于稍微安定了一点。
延安那边,周璇过了几年的幸福日子,终于把“太安”一代又一代传下去了,然后她又跑到华北,进入干部的圈子,再添个小宝宝,叫他“太平”。
以后就是“太和”“娇娇”了,小家伙们一个接一个哇哇落地,打仗还没结束,家里却别说断线,那根绳子根本就没松!

周希汉每回给我发邮件,都是简单的时间和地点,有时还附带一句:“我过得不错。”
有时候会说:“腌菜到了!”
连儿子有没有长牙都不提,更不用说家里是不是跟蒸桑拿似的热了。
她要是觉得不舒服,就让她休息一下嘛。
战场上没得闲,士兵天天走马换将。
这位旅长也换了个阵地,不久就要调走去指挥新组建的部队啦!
回家探亲那次,周璇在门口叫嚷着“你们爸爸”,结果孩子们一个个都懵了,不知道他是啥意思,干脆远远地问:“长官,你是不是姓周啊?”

家里的人一听都乐了,调侃你跟你爷爷学话呢!
那次他待了两天,临走时给每个小孩儿脑袋上抚了一下,啥话都没说。
第二天一大早,扛着个包就出门了,战斗多年,他升职到了高管的位置,也能时不时回家看看,每回到家,饭桌上依旧摆着那瓶酱菜,用老陶罐装着,洗得锃亮锃亮的。
有一天,他找到那张周振喜当初写的便条,纸边儿都快碎了。
他跟小娃娃们嚷道:“这个是你外公写的!”

没人敢去碰那张纸,大家全都围在那儿瞅着。
后来,周振喜撒手人寰了,那张纸条就被裱得漂漂亮亮,安静地挂在家里一个木柜的隐秘角落里。
家里人明白,啥不是单单为那句话的事儿,而是为了那些风风雨雨的岁月,一个爸爸两度冲进战场,就是想看看女婿值不值得把女儿托付!

战乱中交的朋友、咸菜瓶里藏的情意、小纸条上的嘱托,统统埋在那段悄然无声的时光里。

没哇眼泪,也没说情话,一个家就这么在打枪声中悄无声息地苟活着。
等到一切都平静下来,那张纸条还在,跟新的一样没变!
#夏季图文激励计划第二期#
配资安全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